|
Re:qintao |
三皇五帝考辩(续)
山东曲阜孔子博物院 彭庆涛
尧舜禹时代与阶级分化的完成
从古籍资料中大体可知帝尧和帝舜是活动于共同的历史舞台上,略有先后。而且,尧舜与禹相接,禹与夏代相接,或许文献不一定这样表述,但从社会发展史上看,家庭奴隶制王国已走到了尽头。即阶级分化基本完成,上层建筑的巩固和完善已具有国家的性质,甚至有学者认为尧舜时期应属奴隶制社会。因此,这一时期如与考古学相对应,则属于龙山文化时期。
龙山文化的研究结果表明,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关系及经济结构的变化,从而导致了上层建筑的进一步完善,控制上层建筑的家长及其所任用的助手帮凶对奴隶的剥削,也从家庭氏族公社时期的隐蔽状态下逐渐暴露出来,成为奴隶的强制性劳动所占有劳动成果的剥削手段。这样,多数人的劳动成果被少数人所占有,及至多数人的人身也被少数人所占有,便使这些被少数剥削者占有人身的多数劳动力沦为奴隶阶级,而占有多数人人身及其劳动成果的少数统治者便成为奴隶主阶级。尧舜时期就处在这一社会变革时期。
儒家经典中记录的有关尧舜禅位之说,是后人特别是两汉之际王莽秉政以后,刘歆为谄媚于王莽而大吹“禅让”并将其美化了的东西。其实军事民主制度仅仅是出于统治和战争的需要不得已而为之,当阶级分化完成以后,长期降服性质的战争便转化为统一的性质,其社会政治制度发展趋势也就必然向“传子制”的奴隶制国家发展。在战争中联盟首领之一的军事首长的地位得到加强,在他周围,逐渐聚集了一批专以战争为职业的亲兵将领,形成了一个能够掌握整个联盟命运的亲兵集团,即军队。尧死以后,舜曾让避尧子丹珠于“南河之南”,但那些“不之丹朱而之舜”的诸侯“朝觐者”、“狱讼者”、“讴歌者”们,应是舜即位前就已控制在自己身边的亲兵集团首领。这才是真实的历史。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尧和舜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家庭奴隶制时期的上层建筑是方国及联盟政治,尧、舜之间的关系至少能确定他们是同一氏族的相继领袖或相邻方国联盟的相继领袖。因此,他们的郡望不会相隔太远。
龙山文化的发掘资料(包括山东龙山文化和中原龙山文化)告诉我们,山东龙山文化在原大汶口文化分布区域是较为均衡而先进的,这一区域已涵盖了河南东部地区,而豫西及中原大部分地区的龙山文化,则有明显的地域差别,且在中原各文化类型之间,外形上差别较大,均带有地域性的独立性,这是夏前氏族方国林立的铁证。尧、舜之间的关系应能确定,不管他们是同族或是异族,其文化遗存的性质、特点、类型等,表现在龙山文化上,应是同一的。因此,在确定尧、舜的郡望时,首先看他们是否在龙山文化区域范围之内;其二,看二者定位点有无龙山文化为证;其三,看二者文化类型是否为相近区域的同一类型。
另外,还要说明的是,黄帝以后,黄族势力拓展到整个中原,但那只是形式上的统治,而并非经济意义上的统治,首先是父系氏族制度的蔓延,由汶泗流域向外拓展。其次是以邹鲁为中心的大汶口文化区域的父系氏族,多有向中原迁徙的痕迹,这种迁徙绝非完成于某一代人,且所迁之域,大多为典型龙山文化区域,包括山东全境、河南东部、江苏北部、安徽北部、河北南部等。至于某一族人之后裔的迁徙,则多有之,且三代之际,常有封圣君后裔之说,所封之地多以原族称之,其山、水地名亦然。是故古代圣君传言出处甚多,亦不足为怪。
一、有关尧帝的文献记载与遗迹
《史记正义》说:“尧都平阳,葬成阳”。一般认为平阳在山西临汾,古属冀州之地。《史记•五帝本纪》称:“舜,冀州之人也。”由此尧、舜均为冀州之人。又《左传•哀公十六年》引《夏书》曰:“唯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灭而亡。”这样亦可证尧属“冀方”。无独有偶,在汶泗流域也均有有关尧和舜的足迹,细细推敲和琢磨,这里的尧舜踪迹绝非附会之辞,而且更近历史的真实。
《左传•哀公二十七年》载:“越子使后庸来聘,且言邾田,封于骀上。二月,盟于平阳”。注云平阳有二,分东西平阳,泰山有平阳县为东平阳,高平南有平阳县,为西平阳。西汉于此没平阳县,东汉改南平阳侯国,晋时瑕丘入南平阳,北齐撤高平、平阳二县并入瑕丘(今兖州)和邹县。此证一。
又鲁城东有平阳,《竹书纪年》曰:“惠成王十九年,齐田聆及宋人伐我东鄙,围平阳。”亦为鲁东之平阳,此证二。
《元和郡县志》记:“尧祠……在兖州瑕丘南,洙水之右。”《滋阳县志》说尧祠“在县城东七里,今属曲阜县”。《滋阳乡土志》又谓尧祠“在郭家村,汉熹平四年建,宋治平元年重修”。清修《兖州府志•祠庙志》云:“尧祠在城东七里,不详所创。唐翰林李白有尧祠诗,宋学士李昉有尧祠碑记。”此说四款均称尧祠在曲阜兖州之间。此证三。
《史记•五帝本纪集解》云:“案《皇览》曰尧冢在济阴城阳,刘向曰尧葬济阴丘垅山,《吕氏春秋》曰尧葬谷林,皇甫谧曰谷林即城阳”,“《括地志》云‘尧陵在濮州雷泽县西三里’,郭缘生《述征记》云‘城阳县东有尧冢,亦曰尧陵,有碑是也’。《括地志》云‘雷泽县本汉城阳县也’”。由此确定尧冢在今钜野西而定陶之北。明修《兖州府志》亦曰:“雷泽本汉城阳县也,欧阳修所考后汉尧祠碑云李树连理生于尧冢及尧母庆都墓,亦在济阴灵台,以此推之,则尧陵在曹濮境上明矣。”此说济阳不仅有尧陵,且有尧母庆都之墓。此证四。
又见《泗水县志》、《泗水地名志》均载泗水有尧山,又名无影山,“世传为尧王之坟墓”,如此载无误,此地当为尧部落的源头。再看尧王二墓之位置,其一在东域,其二在西邻(现属鄄城),曲兖之间则有尧祠,所征邹鲁为尧王故地,亦不偏颇。此证五。
《史记•五帝本纪》索隐又记:“尧,谥也,放勋,名。帝喾之子,姓伊,祁氏,案皇甫谧云尧初生时其母在三阿之南寄于伊长孺之家,故从母所居为姓也。”此言尧帝的初生地应在“三阿之南”。据明修《兖州府志•沿革志》:“定陶县,古三朡国也,本尧所居。”其地北隔大野泽(亦称雷泽)有柯地,亦称阿,现有东阿县。当为《索隐》所言“三阿”之地。如是,则定陶应为帝尧故地。此证六。
定陶县,古称陶丘,亦称陶。尧所居,其后迁唐,故称陶唐氏。《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徐广云:号陶唐;《帝王纪》云: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徐才《崇国都城记》云:唐国,帝尧之裔子所封,其北,帝夏禹都汉,曰太原,郡在古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其南,有晋水;《括地志》云:今晋州所理平阳故城是也。平阳,河水。一名晋水也”。由引文可知唐国为帝尧之裔子所封,而非尧所都之地。又晋水、河水称平阳者,其解确有偏颇之处。晋南之平阳出处有史可征,《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晋韩宣子卒,魏献子为政,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赵朝为平阳大夫……”。这就说明晋之平阳县是春秋时分羊舌氏田为三县,其一为平阳县。隋朝改称临汾。唐王朝发迹于临汾,为抬高其郡望,亦将晋之平阳改做尧都,并建庙祭祀。又古唐国确有尧之后裔,相传殷末周初之际的鄂侯乃陶唐氏之后。因尧之后裔封唐国,逐将陶、平阳等称谓呼其族和所居之地,故有陶唐氏、平阳等。此证七。
根据文献记载,尧帝为颛顼之子,或为颛顼之族人,颛顼都城由曲阜迁于濮阳,其子或族人随至濮阳附近之陶丘、鄄城、钜野一带,合情合理。此证八。
帝尧与帝舜关系之密切,可知他们其郡望应相一致,舜源于泗水(见后文),曾迁徙于大野泽附近,尧陵之西亦有舜之踪迹,有历山,有舜庙,有雷泽城,亦有姚虚。泗水源头有尧山、尧王坟,亦有历山、雷泽、桃虚(姚虚)、更有舜生地——诸冯,曲阜有寿丘,兖州古为负瑕,皆舜之迹。汶泗流域及其附近地区,尧舜之迹相互参差,亦可证二帝关系之亲密。此证九。
明修《兖州府志•帝迹志》又云:“尧立为天子以火德王,都于平阳,在位七十年举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于天,避位二十八年而崩,寿一百十七岁,其后有房、铸、蓟、郇、栎、高唐、上唐、镏、杜皆为诸侯,在府境者为铸”,“书曰济北国蛇丘有铸乡城”,“而东平亦有尧陵,不知其所有始也,今东平尧陵正与蛇丘相近”。经查证,铸乡在泰安肥城南,亦近汶水。又高唐、房、铸、栎等地多在山东河南一带,亦证尧出鲁西南之地。此证十。
综上十款,有史有迹,有情有结,有理有据,难以推翻,可证帝尧发迹于此。
二、有关帝舜的文献记载与遗迹
《史记•五帝本纪》曰:“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
若称舜帝发迹之地,必须兼有历山、雷泽、河滨、寿丘、负夏之地,那就依次看来——
历山,《五帝本纪集解》引郑玄曰:“(历山)在河东。”《正义》引《括地志》云:“蒲州河东县雷首山,一名中条山,亦名历山……历山南有舜井。”又云:“越州余姚县有历山、舜井。……二所又有姚虚,云生舜处也,及女为州历山、舜井皆云舜所耕处,未详也。”
雷泽,《集解》引郑玄曰:“雷夏,兖州泽,今属济阴。”《正义》引《括地志》云:“雷夏泽在濮州雷泽县郭外西北。《山海经》云雷泽有雷神,龙首人头,鼓其腹则雷也。”
河滨,《集解》引皇甫谧曰:“济阴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正义》曰:“于曹州滨河作瓦器也。《括地志》云:‘陶城在蒲州河东县北三十里,即舜所都也。南去历山不远,或耕或陶,所在则可。何必定陶方得为陶也?斯或一焉。’”
寿丘,《集解》引皇甫谧曰:“在鲁东门之北。”《索隐》曰:“寿丘,地名,黄帝生处。”
负夏,《集解》引郑玄曰:“负夏,卫地。”《索隐》云:“就时犹逐时,若言乘时射利也。《尚书大传》曰‘贩于顿丘,就时负夏’。孟子曰‘迁于负夏’是也。”
上述资料表明,舜的发迹重点在曲阜、钜野、鄄城、定陶等鲁西南一带,或者说,在汶泗流域与黄河济水交汇的兖豫大平原。
然而,一旦考查舜帝在泗水上游的遗迹,则只能表明鲁西南、豫东为舜的迁徙之地,至于济南、越州、妫州,则应是有虞氏之后裔迁徙或分封的结果。考据如次:
第一,《孟子•离娄下》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人也。”这一记载应比《史记》正义、索隐、集解等早得多,也信实得多。至少可以证明,战国时期人们知道舜为东夷之人,并明确指出舜生于东夷的诸冯,曾迁到负夏,最后卒于鸣条。从而又引出“诸冯”和“鸣条”二地。
诸冯,有人认为是临沂的诸城。其实不然,诸冯在泗水东今平邑域内,现仍称诸冯村。
负夏,亦称负瑕,负瑕周时为鲁邑,汉改为瑕丘县属山阳郡,武帝元光年间封鲁恭王子政为瑕丘侯,故为侯国,晋时入南平阳属高平国,南北朝时宋元嘉中始为兖州治所,即今兖州。
鸣条,古载有二,其一在山西运城安邑镇,其二在河南长垣西南。河南长垣与山东菏泽仅隔济水,一水相望,又古代通属东郡曹濮之地,故应信之。
这样,诸冯、负夏、鸣条三地清楚了,也就不难看出舜帝的活动区域,生于泰沂山系西麓的泗水上游,沿泗河而下,经过兖州,到达菏泽,最后卒于河南长垣。不能不说是孟子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条明晰的线索。
第二,据司马迁《史记》所列帝舜之世系为:黄帝——昌意——颛顼——穷蝉——敬康——句望——桥牛——瞽叟——重华(帝舜),知颛顼、穷蝉、敬康、句望等为帝舜之祖。上文己表,颛顼都曲阜。《泗志钩沉》记“颛顼封其庶子穷蝉於姑幕,徙封少典氏于颛臾”。姑幕在泗水县治东南五十里的姑幕山下,有姑幕城。又记“姑幕传子敬康,至孙勾望浸衰,帝乃封白马于其地,而以一都之地徙封勾望于“郚”。白马是颛顼之孙而骆明之子。郚亦称沮吾。“《寰宇志》曰坨城为古崇国,在泗上,今(泗水)治东北四十里有崇邑,西有城子顶者即坨城故址”。坨城即白马之子鲧所封之崇伯之国,“尧封崇伯兼有少典、姑幕及沮吾之地”61。由此可知,舜之祖颛顼、穷蝉、勾望等均在泗水,那么,舜源于泗水也就无可置疑了。
第三,泗水有历山、舜庙、舜井、诸冯、桃墟(姚墟)、雷泽、娥皇女英台等。《泗志钩沉》载:“历山在治东七十里,雷泽湖南脉自关山中麓南下入湖,湖心有石攒立,入秋后,湖水从石窦泻落,其声如雷,数日,湖水涸大半。湖心之石,殆即地理家所谓崩洪过渡者也。过湖正南起,为历山,其关山东路一支。环湖东滨南与历东之山相接。故湖水虽大不能西溢。山中有历山村,附近有诸冯村,有舜井,有娥皇女英台。”明嘉靖十年《重修舜帝庙记碑》载:“泗邑东南七十里有历山,乃故圣君大舜耕稼之地也。”元代《舜帝庙碑》载:“出泗水县治,溯朝阳而行,八十里之遥,有山曰历山,世传为舜帝所耕之地,其旁九男之渚,二女之台,遗迹者甚多,山之东有祠,有石刻金大安元年重修也。”又有明碑记:“泗邑东去封内七十里,有历山,山之左有民舍千余家,自古为集。村依山名焉,为先帝大舜耕、陶、渔之处也。”上述所记地名,与舜帝所涉地名无不一一相附,若非舜生之地,岂能如此完备、系统而巧合哉!
第四,有关舜“作什器于寿丘”,史书多有记载,因前文多有列举,故此不作铺陈。寿丘在曲阜,即黄帝所生之地。至于“陶河滨”,可见《韩非子》“东夷之陶若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可知“河滨”亦在东夷。又泗水有桃邑,古称陶墟、或桃墟。《左传•襄公十七年》载:“齐国伐我北鄙围桃。”杜预注:“鲁国卞县有桃虚。”《水经注》曰:“泗水出卞县故城东南,桃虚西北。”桃、姚二字相通,故知桃虚亦为姚虚。又桃、陶音同,故桃邑亦为舜“陶河滨”之处。又泗水有柘沟,柘沟制陶业历史悠久,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素有“陶乡”之称,文物部门考证,此处早在五千年前已形成聚村,有大汶口文化遗址为证。当谓舜帝始“陶”之所。
第五,再以皋陶、伯益父子为证。史载:
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62
皋陶生于曲阜,曲阜偃地,故帝因之而以赐姓曰偃。尧禅舜,命之作士;舜禅禹,禹即帝位以咎陶最贤,荐之于天,将有禅之意,未及禅,会皋陶卒。63
曲阜人皋陶是舜的助手,奉命与禹同治水土,如果不先禹而卒的话,便将继禹而兴。皋陶偃姓,偃、赢音转,应为少昊同姓,说明皋陶出于少昊族。其子伯益也是夏初的一个突出人物,《夏本纪》说得非常清楚:
(皋陶卒)而后举益,任之政。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
伯益与皋陶不同,业已代禹而立,执掌天下,尔后让位于启。皋陶、伯益为曲阜人,其佐舜之域当为近地。《泗志钩沉》云:“帝封鲧叔父白犬之子卞明于其地,以奉颛顼之祀,历夏及商。汤伐有卞,存其祀,分其地封皋陶子伯翳之裔费昌为奄国,兼有今县西及曲阜、邹、费之境。而卞明、颛臾、鄫、邾错处其间,为附庸。皋陶本偃人,赐姓偃,伯益封费,赐姓赢。奄与偃字通,而国为赢姓。”
由此可知,皋陶、伯益与舜,同起于泗水之滨。
第六,泗水元、明时期,多有碑刻记之,如元代孟从仕《重修舜宫记》、《金大安元年重修碑》等。多有真知灼见,不乏其考。现附录一二,以证其事。
明代贺逢吉《帝舜历山辨》:
按舜耕历山记载不一。《山东通志》博综审核,一以为在濮州;一以为在冀州河东;一以为在齐地。而卒以濮州为正,并无一语及泗。惟祠内载有舜皇庙云。夫三者之说,或取诸应劭,或取诸郑一,或取诸皇甫谧。而竟未闻以孟子之说为正者。孟子不云乎,“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东夷之人也”。又云:“自耕稼陶鱼,以至为帝,无非取诸人者。”朱子解曰:“耕于历山,陶于河滨,渔于雷泽”。今考本县历山之东,有费县诸冯村,是舜所生处也;兖州古瑕邱,即负夏地,是所迁处也,历山沃饶是所耕处也;泗河之滨有上涧柘沟,称为名陶,是所陶处地也;历山东北,为巨湖,每遇盛夏,弥漫无涯,霜降水涸,声震原野,是所渔之处也。以是地而质诸孟子之言,若合符节矣。于今历山有帝舜庙及娥皇女英二台。虽亦详所始,而宋金元三朝有重修碑记,称帝里云。诗曰:“维岳降神,生甫及甲”。我泗山川,故称奇异,有帝舜遗迹在在可稽,独奈何不辩?且孟子即曰:“舜,东夷之人也。”又曰:“舜之居深山之中”。冀州河东,姑置无论,既濮州、济南,孰有在吾泗之东者?濮州、济南之山,孰有深于吾泗者草茅?管窥必以舜为泗人无疑。敢冒论之,以俟考古君子或于鄙言有取焉。
明代尤应鲁《历山考》:
余按山东通志及府志,历山凡三见。而泗不与焉。一在冀州,一在济南,一在濮州。据二志所参定,皆谓历山在濮州。盖本于《援神契》:“舜生姚虚。”应邵“姚虚与雷泽相近”之言也。姚墟在濮,与历山、雷泽、河滨、负夏相望。故谓舜之耕历在濮。而谈济南、冀州者皆退矣。第于吾泗亦未之深考焉。夫舜生于诸冯,而今曰舜生姚墟,盖谓诸冯之姚墟也。语见本府帝迹志,其说是矣。今濮州亦有诸冯乎?余考费县有诸冯村,离泗十里。而《水经》云“鲁国卞县东南有姚墟,世谓之陶虚,井曰舜井。墟东有漏泽方十五里,渌水泓渟凡三。大泽西际有阜,俗谓之妫亭山”64。由此观之,则泗固亦有姚虚矣。孟氏曰:“舜之居深山之中。”余观濮州多泽国,深山二字,恐濮与泗自当有辩。雷泽在历山之北,虽非禹贡之雷夏既泽,而湖面方十五里,秋冬水涸,响声若雷,名固不虚。再读唐人过河滨赋云:“步出城西门,徘徊见河滨。当其侧陋时,河水清且潾。至化无若窳,宇宙将陶甄。”则泗河之滨良舜所陶处也。水经又云:“负夏即瑕邱,为今兖州府城。”则负夏固濮、泗共之矣。故舜庙、舜井、妫亭山、娥皇女英台,皆在泗,历山遗迹尚在。自宋而金而元俱有遗碑,称帝里云。余登历山渴帝舜庙,询之老成人,咸谓此庙十里之内,蝗蝻不入境,冰雹不降灾,傥所谓圣迹是耶非耶?再考府志所述《水经》“鲁国卞县东南有桃虚”,与《天中志》所载,水经姚墟,姚桃不同,以愚意度之,桃与陶音相类,陶与姚,音相类。讹以传讹,所从来旧矣。则以桃墟即为姚虚,亦未为牵合附会之说也。而况《天中志》又促征之。因并述之以备参考。
第七,有关舜生泗上之说,历史上多有考证,但因应劭、郑玄、皇甫谧等名家者言,影响甚大,加之孔安国、司马贞、张守节等唐代学者及宋裴骃等人附合其说,遂以正史流传,后人趋之为宗。而藏山窝中的泗水县地却鲜为人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山东省图书馆藏有清末光绪年间泗水知县王子襄先生《泗志钩沉》一书,分《山川考》和《泗水疆域沿革考》两部分,详细论述了泗水境内的皇古遗踪,颇有参考价值。此书未正式出版,据本书中眉部附言记“吾师王子襄先生尝手书此铭,付邑人王文楼君选石镌诸良常山之麓,迄今未果。予尝借录一通,惜不在手下耳”。略款为“源附识”。有此可知《泗志钩沉》为手抄孤本之书。亦不为世人多知。
已故历史考古学家王献唐先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曾亲临泗水、曲阜、邹城一带考查,并著有《炎皇氏族文化考》一书,该书从多学科的互相参照中,对有关记载上古三皇五帝等史迹的文献资料作了详尽的考辩,虽然有些观点尚有商榷之处,但其资料之充分,论证之扎实,表现出独特的见识和一代学者风范。书中所列八证以明伏羲、帝舜源于泗水,是为一大贡献。
综上七款,足以证明泗水是舜部落的发迹之地。至于曹濮之地,亦有舜帝的遗迹多处,而史书多以此地为舜帝之都,这与泗水为舜之故地并不矛盾,恰恰证明了舜帝或舜部落迁徙的历史事实。
首先,自炎、黄、蚩尤逐鹿中原以后,鲁中南、鲁西南即汶泗流域的父系氏族部落,沿河、济之水向中原方向迁徙。先是颛顼自曲阜迁徙濮州,散见于多种文献记载;紧接着是帝尧迁徙陶丘,尽管文献对帝尧迁徙之事记载较少,由前文足可证之;然后是舜帝迁往曹濮,可以断言,舜帝部落在曹濮地域活动时间较长。在尧舜迁徙以后,将原地的山名、泽名、地名等亦带到曹濮之地,逐有历山、雷泽、姚虚、舜井等地址遗迹。以后,其后裔不断外迁,并在各地发展,为追忆其故乡,遂将当地之山称历山,当地之渊称雷泽,等等,有山无泽之地,则选其近者称雷泽,有泽无山之地,则选其近者为历山。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不可能把所有的地名都带走,故而到汉代考证时,因孟子所言与其考证甚远,故而不提。如将孟子语及汉人所追之地名括在一起,则不攻自破,唯泗水上游兼有之,集诸冯、姚虚、雷泽、河滨、寿丘、负夏、历山、舜井、舜庙、娥黄女英台等众多遗迹之名为一地者,其他任何地区,均难与汶泗流域的邹鲁相匹。唯孟子言舜“卒于鸣条”不在汶泗流域,加之曹濮舜帝之迹,岂不恰好证明了帝舜迁徙之事实么!其次,考古发掘资料的日益丰富,越来越多地证明了大汶口文化区域率先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并以相当快的速度向外幅射。到龙山文化时期,山东及河南东部、苏北、淮北、冀南等地,形成了文化内涵与特征比较稳定而统一的海岱文化区域,这都充分证明了鲁中南父系氏族向中原迁徙的客观事实与社会效应。
三、尧舜禹时期的军事民主制时代
尧舜禹时期是父系氏族制的成熟和完备时期,它标志着原始社会行将走进它的末日,国家文明悄然取而代之。当时,全社会的生产和生活都是通过氏族、胞族、部落或部落联盟等民主性质的管理机构加以协调。这些机构的首领如尧舜禹等,是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渐由民主推选出来的。在管理部落时,主要依靠其声望和传统习惯力量,而每一重大决策,只有在公众认可的时候才能有效,不然便被否决。《尧典》、《史记》所载,尧在部落议事会上,商议治水和帝位人选时,还常被“四岳”所否定,不能独行其事,只得服从众岳意见。可见原始民主制对联盟首领的约束力。并且,由于父系氏族时期为集团所有制,流行掠夺战争,使当时的社会既有氏族民主的传统,又有军事性质,故称当时为军事民主时代。
孔孟极力强调“禅让”,“唐、虞禅,夏后、殷、周继”65。而《纪年》则有“舜囚尧,复偃塞丹朱”的记载。韩非子更说“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之弑其君者也”66。
固然不可否认在复杂的新旧交替过程中,“四岳”诸伯之间凭借强力争权夺势,但又必须看到,那时尧舜只能将私有财产传授其子,还不能把天下(王位)看作自己的私有财产让儿子继承。倒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氏族成员及其部落之间平等、民主、利益一致的关系遭到破坏,社会出现了统治阶级的联合,当掌握了至高无尚的权力以后,便有父系制的根源——血统,决定其必然要向“传子制”发展。“天下为公”则转变为“天下为私”。如果尧舜生逢阶级对立之时,他也会把天下授给其子,而不管其肖不肖了。换言之,父系氏族社会孕育了私有制,而私有制的发展又直接破坏了氏族公社的公有制,从而产生贫富两极分化,导致阶级的对立和残酷的压迫,加速了氏族制的瓦解和奴隶制的形成,延续二、三百万年的人类史前时代终于走到自己的尽头,人类社会就要跨进国家文明的门槛。
恩格斯对古希腊分析之后,从四个方面论述了氏族制度的解体,具有普遍意义:其一,由于子女继承财产的父权制,促进了财产积累于家庭中,并且使家庭变成一种与氏族对立的力量;其二,财产的差别,通过世袭显贵和王权的最初萌芽的形成,对社会制度发生反作用;其三,奴隶制起初虽然仅限于俘虏,但已经开辟了奴役同部落人甚至同氏族人的前景;其四,古代部落对部落的战争,已经开始蜕变为陆上和海上为攫夺家畜、奴隶和财宝而不断进行的抢劫,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67
所以,氏族制度瓦解的过程,也是国家形成的过程,而战争又成为国家诞生的助产婆。
战争对于军事首领来说,不仅加强了其自身的政治地位,也获得了比其他部落显贵们多得多的奴隶与财富,强化了自己的疆域和力量。尧、舜、禹时期的三次部落联盟战争,促进了父系氏族社会制度的瓦解和奴隶制的形成,使战争的性质由降服、掠夺转为统一,向国家制度过渡。尧时曾经打败过丹水之浦的三苗,欢兜降服了,加入了尧的部落联盟,尧的儿子丹珠担任了丹水部落的军事首领68。舜时又与三苗大战,三苗败,舜则把他们疏散到北方“更易其俗”而进行同化69。禹的时候仍与三苗冲突,《墨子•兼爱下》引“禹誓”云“济济有众,咸听联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即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打败三苗后,使三苗从此一蹶不振,禹则“辟土以王”了。
军事民主制时期的频繁战争,在考古资料中也有所反映。如河南登封王城冈的小城堡;河南淮阳平粮台的城址;陕西客省庄遗址六个灰坑中埋有人骨架,放置极不整齐,有的无头,或人、兽葬在一起;洛阳矬李也有灰坑中埋人的现象。邯郸漳沟发现了几个圆形葬坑,有一个在红烧土下埋十具无次序叠压的骨架,都为男性青壮年或五至十岁的儿童,其中有的头骨上有被砍的痕迹。还有一圆坑极不整齐地放置男女老幼骨架五具,有的身首异处,有的呈挣扎状。另有一半地穴室的炉灶周围,放置四个人头盖骨;山西襄汾陶寺类型龙山文化遗址提供了原始社会瓦解和阶级、国家产生的具体例证,700多座墓中,大中型墓占89座,其中大型墓仅有9座,占全墓总数的1.3%。大型墓主都是男性,长方形墓坑内使用木棺,底铺朱砂。随葬品有彩绘龙盘、成套的彩绘木器、陶器和玉石礼器、武器、装饰品和整猪等达上百件之多,而小型墓则一无所有。足见强与弱、贫与富、首与众的巨大悬殊,反映出家庭奴隶制向奴隶制国家的转变。
四、治理洪水与国家的诞生
根据史料记载,我国国家的诞生,不仅部族间的战争起了催化剂的作用,而且亦与大规模治理洪水有关。其治水的重点区域,则是黄河下游以鲁西南为中心的兖豫大平原。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70。尧独忧之,“求能治水者,群臣四岳皆曰鲧可,……于是尧听四岳,用鲧治水。九年而不息,功用不成。于是帝尧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摄行天子之政,……于是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71。于是出现了大禹、契、皋陶、后稷、伯益等众多首领联合平治水土的轰轰烈烈的场面。由于皋陶贡献巨大,禹立皋陶“且授政焉”,不幸皋陶卒,“而后举益任之政”。可见,军事民主制时期的禅让传承,以及联邦制度的建立,奴隶制王朝的诞生,是在治水过程当中逐渐形成的。
这是因为,国家与旧氏族组织的不同之点,一是按地区划分居民;一是有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变堙障为疏导,引流水入东海,就必须大面积大流域地统一规划、综合治理。治水大军的车轮必然要碾碎打破过去那种孤立保守、画地为牢的氏族群体的分隔界限,建立并维护以治水为目的的职能领导机构,运行这种公共权力,即由一个联合统一体凌驾于各方之上以指挥“天下万国”,按照层层组织的权力高下,分配治水斗争的任务和胜利成果。由此便孕育、演变成为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政权。也就是说,为适应治水斗争和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促成了我国奴隶制的早熟。
注释:
1 《汉书•古今人表》
2 《古代社会断代新编》第53页,1982年人民出版社
3 《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4 《左传•僖公二十一年》
5 《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54页
6 《白虎通》
7 《中国政治制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
8 《韩非子•说难》
9 《周易•系辞下》
10 谯周《古史考》
11 《礼记•曲礼•正义》
12 《史记•五帝本纪•索隐》
13 《逸周书•尝麦解》
14 《大荒北经》
15 《大荒东经》
16 《大荒东经》
17 《大荒北经》吴任臣注引《广成子传》
18 《太平御览》卷一五引晋虞喜《志林》
19 《大荒北经》
20 《史记•高祖本纪》
21 《山海经•大荒南经》
22 《云笈七笺》卷一百《轩辕本纪》
23 《梦溪笔谈》卷三
24 《史记•五帝本纪》
25 《河南偃师“滑城”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64年第1期
26 《郑州大河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
27 《河南禹县谷水河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9年第4期
28 杜金鹏《关于大汶口文化与良渚文化的几个问题》,《考古》1992年第10期
29 《中国古代历史地图册》,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页
30 武津彦《略论河南境内发现的大汶口文化》,《考古》1981第3期
31 《山海经•大荒东经》
32 《帝王世纪》
33 《尸子•群治篇》
34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35 《尚书•正义》
36 《帝王世纪》、《春秋元命苞》、《初学记》
37 《史记•周本纪•集解》
38 《拾遗记》
39 《史记•五帝本纪》
40 明万历《兖州府志•帝迹志》
41 明万历《兖州府志•帝迹志》
42 清修《阙里志》
43 清修《阙里志》
44 《史记•五帝本纪》
45 《山海经•海内经》
46 《帝王世纪》
47 《山海经•大荒东经》
48 《山海经注疏》•郝懿行注
49 《国语•楚语下》
50 《考古学专题六讲》,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
51 《大戴礼•五帝德》
52 郭沫若《金文丛考》
53 《五帝本纪》
54 《五帝本纪》
55 《殷本纪》
56 《周本纪》
57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
58 《史记•五帝本纪》
59 《甲骨文所见商族鸟图腾的新证据》,《文物》1977年第2期。
60 田昌五《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论•先商文化探索》
61 《泗志钩沉》
62 《史记•夏本纪》
63 《正义》引《帝王纪》
64 见《天中志》
65 《孟子•万章上》
66 《韩非子•说疑》
6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04页
68 见《吕氏春秋•召类》
69 见《韩非子•五蠢》
70 《孟子•滕文公上》
71 《史记•夏本纪》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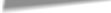 |
回复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