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e:本周话题:你了解她吗? |
韩非 文 / 柳树下的童年
李宗吾先生写过一本《厚黑丛话》,乃续《厚黑学》而来,其中有这么论先秦诸子的一段:“老子在周秦诸子中,如昆仑山一般,一切山脉,俱从此处发出。韩非如东海,为众河流之总汇处。其他诸子,则为一支山脉,或一条河流。”这个比喻非常独特有趣,又说:“道法两家的说法,根本上原是相通,敛之则为老子之清静无为,发之则为韩非子惨烈。”“韩非之书,对于各家学说,俱为批判,足知他于各家学说,都一一研究过,而后才独创一说。”都是有见地的评论。很多人认为韩非是法家的集大成者,其实不然,若熟读《韩非子》一书,可知除商鞅、慎到、申不害外,老子、墨子、荀子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过韩非。韩非的哲学,并非单纯的政治哲学;韩非的主张,亦非单纯的法治;韩非本人,更不是有手腕无感情的政治家,他的学问、他的见解、他的卓绝的智慧、他的深刻的观察,在先秦诸子中都是独树一帜的。
一、身世
先秦诸子,凡我知道的,除韩非外,没有一人出身贵族。孔子的父亲是一介武夫,在孔子三岁时他就去世了,所以孔子小时贫寒,常为人相礼、料理丧事,还做过替人管理仓库的“委吏”,看管牧场的“乘田”,后来他回忆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见《论语》,《子罕篇》)。孟子也是三岁丧父,他母亲把他拉扯大,“孟母三迁”的故事是人所共知的,想来其境况也必定十分清苦。庄子呢?漆园小吏,还曾编草鞋糊口,他的穷窘可想而知。墨子是贱民,那就更不用说了。
与前面几人相比,韩非就要显贵得多,他是韩国的公子,且曾拜大学者荀子为师,与韩非同窗。但,出身高贵对于韩非来说,未必是一种福气。韩非的童年是缺乏爱的,这可以从他的文章中找到证据,“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见《韩非子》,《六反篇》),这是一个忧郁自闭的孩子对自己那奔走于名利场中的父母的冷峻的观察。又“人为婴儿也,父母养之简,子长而怨;子盛壮成人,其供养薄,父母怒而诮之。子、父,至亲也,而或谯或怨者,皆挟相为而不周于为己也。”(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我读到这里,已经开始冒冷汗了,父子至亲,尚且如此,足见韩非一生都不曾得到过别人的关爱,所以才会形成这么冷刻的看法。
韩非口吃,可知他小时一定受过不少人的嘲弄,以至对人世间“爱”这种东西的存在表示怀疑。非又曾上书韩王,王不能用,于是观往者得失之变,发愤著书,终大成,秦始皇见而叹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为得韩非,秦急攻韩国,既得之,又为李斯所忌,不能用,下狱而死,时年四十七岁。
后世儒者往往嘲笑韩非的死是罪有应得,原因是韩非曾反对和挖苦过孔孟“仁义”的主张,但我想,那些所谓的传承圣人之道的家伙,他们每天高谈阔论,嘴边挂满了“仁义礼让”之类冠冕堂皇的字眼,一面端坐在大厅里“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地大吃大喝,一面又说着什么“君子远庖厨”的漂亮话,最后再招一帮徒弟,开馆讲学,安安稳稳活到七八十岁。这种生活方式,以韩非的才干,并不难求得,只是韩非秉性刚直,不屑为之而已。
那么,归根结底,韩非为什么会被杀呢?李宗吾说,世事可分两种:一种做得说不得,另一种说得做不得。前者如夫妻房事,夜深无人之时尽可大做特做,但拿到人面前说,就是笑话,所以萧伯纳说:“真话就是笑话。”后者如张三骂李四曰:“我X你妈。”这种话尽可以说,但要动手去实行,那就不成体统。韩非恐怕是把实话说出来了,所以在伪君子们看来非杀不可。
好,下面我们就看看,韩非到底说了些什么大实话。
二、“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
先秦诸子中,孟子主性善,荀子主性恶,墨子则以人性若素,无善无恶。韩非既师承荀子,当然也主性恶,但他的性恶比荀子更冷酷、更彻底。
荀子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见荀子《性恶篇》),也就是说,人性向恶,可教化使之善。他在这一点上显出儒家本色来,他主张一个“礼”字,因为有了礼的节制,人就可以向善了,所以胡适认为:“荀子虽说性恶,其实是说性可善可恶。”(见《中国古代哲学史》第十一篇)。
荀子主礼,韩非主法,礼与法不同,“夫礼者,所以正君子也;法者,所以治小人也。”(见袁准《治乱篇》)。荀子虽说性恶,仍以天下人为可教化之君子,所以主张兴礼,而在韩非眼中,人与人之间就只有利害打算,连最基本的一点善心都没有了,所以必须用严酷的法来治理他们。比如在《备内篇》中,韩非形容世人道:“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党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则势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这是个多么冷酷扭曲的世界!但我们得承认,韩非说的都是实话,事实就是如此。
不过,从当时那个角度看,法治也的确比礼治要先进得多。因为礼治即人治,它没有强制性和客观性,对于即将到来的封建时代,它已经无法适应了。法治却不同,所谓“刑过不避大夫,赏善不遗匹夫。”(见《有度篇》),即是其平等性的表现,于是,下层百姓为国效力的积极性就也被调动起来。然而,中国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一直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有效的法治体系,韩非之学,亦被斥为异端,这恐怕就是社会弊病、国民劣根经久难除的一大原因。
三、“上古竞于道德,中古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
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在商讨御侮事宜的时候,大学士倭仁提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当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对抗强敌。这位大学士想来是四书五经读多了,人家坚船利炮已经打将过来,你还要讲什么“忠信礼义人心”,岂不知“枪杆子里出政权”,要自强,没有先进的武器,没有勇猛的军队,空谈儒术,是半点用处也没有的。
春秋战国,是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的一个动荡时代,很多事情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感此,先秦诸子纷纷提出自己的主张,以求治国平天下。孔孟主张“仁义”,这显然是迷恋于上古道德之世而产生的幻想,不切实际;老庄主张“无为”,要返回“小国寡民”的原始时代,那就更加遥远了;墨子本是我最为崇仰的,他的略带无产阶级性质的政治主张最为激进,只可惜他仍然要“明鬼”,倡“先王之道”,这一点上做的也不好。
韩非,只有韩非,他深刻地观察出历史的演变不居,提出“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见《五蠹》),“时移而法不易者乱;世变而禁不变者削。故圣人治民也,法与时移,而禁与世变。”(见《心度》)。他还嘲笑孔孟复古的主张为“守株待兔”,这一冰冷的幽默刺得儒生们痛了整整两千年。
权变,是韩非思想的精髓,知道了“当今争于气力”,也就知道了如何才能吞并六国,以及天下必然走向大一统的形势,这方面,秦始皇可以说是韩非的知音。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提出:“国君之立丰功伟绩者,皆不重信,而以诡诈行事。凡竞争之术不出两途:一以法律,一以暴力。用法律者,人也;用暴力者,兽也。然而法律之力常不足,则不能不用暴力。有国者宜兼用人兽竞争之术,否则不能永保其图。是故国君宜权变。”这是实话。达尔文说:“适者生存。”这一原理用于自然界,即是进化论;用于政治界,即是权变论,所谓政治者,与两头长颈鹿争吃树叶,颈长者胜、颈短者败的道理,并没有什么不同。
四、“明主举实事,去无用,不道仁义者故,不听学者之言。”
先秦诸子各有自己的一套价值观,孔孟老庄皆贵虚,惟有墨子韩非的价值观是实用功利的,他们要求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试以吃饭论,吃饭最重要的是什么?如果是孔孟,他们会说,重要的是过程、是品味;如果是老庄,他们会说,吃饭就是吃饭,不要存什么高下轻重的心思;而墨子韩非则会认为,吃饭只是为了填饱肚子,没有别的。我记得东晋名士,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居会稽时,尝雪夜泛舟剡溪,访戴逵,至其门而返,人问其故,曰:“本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安道(戴逵字)耶?”话说的很堂皇,其实他还是不想访友,若一心思念友人,又岂有兴尽之理?或许他只是想借此赏赏雪景并故作高深赚点名声吧。
墨子是为天下苍生求利,韩非则是为君主求利,性质上大不相同。比较而言,墨子当然更值得我们佩服,但韩非的那套方法,却是政治界的一棵常青树,不可不研究。怎样求功利呢?墨子认为人人都应该劳动,不能做“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儒生,并杜绝奢侈浪费,反对文藻华饰,这样才能进而为大同治世。韩非没有那么平民化与理想化,他依然主张以法治来求功利,也即利用法的权威,将不利于君主统治和社会发展的种种因素都除去,对于目无法纪者,严刑处之,杀一儆百,最终达到“以刑去刑”的目的,进入一个人人守法,步步向前的社会。从一定意义上说,韩非的这些主张接近于西方的实用主义,如皮尔士、詹姆斯、胡克、还有杜威,他们认为,一切知识都起源于经验,经验才是最真实的存在,应该以功利为标准确定真理。一种概念,只要能顺利地转移经验,将事物完满地联系起来,能简化劳动,在行动中有用,那就是真的。认识和真理并不是绝对的目的,而只是在行动中获得成功的手段。如皮尔士就说:“任何观念的意义就在于它所能达到的实际效果。”(见《皮尔士文集》)。事实上,我们工作、学习、娱乐,也无不基于一种功利实效性的目的,没有谁会真的认为“贵在参与”,倒是马基雅维利的所谓“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常常被拿来使用,只是人们不说出来罢了。
价值观的功利性和实用性必然导致知识论的实证主义倾向,这一点在韩非和墨子身上都有应验,韩非说:“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见《显学》),他反对未经实践便下断言,这实质上继承了墨子的三表法,“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见墨子《非命上》)。
五、《韩非子》
最后来说说这本书。
《韩非子》,汉书载为五十五篇,今本亦五十五篇,但多有可疑之处,如《初见秦》记张仪劝秦王攻韩的话,用意与《存韩》完全相反,不像出于一人之手。再如《有度》记楚、齐、燕、魏四国之亡,而韩非死时它们尚未灭亡,这就更加可疑了。不过,总体来说,《韩非子》的结构与风格是稳定的,主要应为韩非所作,或许后人略加以附会,遂成今本。
风格上,《韩非子》具法家风范,逻辑严密,论证扎实,间杂以寓言阐明事理,往往透出一种冷冽的幽默。因了个人遭遇的特殊,韩非的文章充满抑郁悲凉之气,明人茅坤评之曰:“沉郁孤峻,如江流出峡,遇石而未伸者,有哽咽之气焉。”是有见地语。
此外,韩非还有一些重要主张,如“法、术、势”的运用、循名责实及人设之势等,本文未曾提到。一来笔者才力有限,篇幅亦有限,不能将一个完整的韩非展现出来;二来他的某些主张对今天来说已不适用,所以不提。但,不管怎么说,韩非都是先秦诸子中顶杰出的一位,我愿以林语堂先生的一句话为本文作结:“半部韩非治天下。”
(转自“红袖添香”)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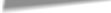 |
|
回帖 |
 |
|
| 回复人: |
姜辛 |
Re:姜辛 |
回复时间: |
2003.11.11 12:26 |
|
红袖网友 柳树下的童年 评论于2003-6-14
附:韩非(约前280—前233),韩国的贵族,荀子的学生,生活于战国末期。起初秦始皇读他的著作,十分佩服,邀他来到秦国。他的同学李斯恐怕他被重用而动摇自己的地位,将他陷害入狱,最后自杀于狱中。他的著作《韩非子》,是先秦法家的代表作,共五十五篇。
韩非虽师从荀子,思想差异却很大。他综合了申不害、商鞅等人的思想,发展成为自己完整的理论,着重谈治国的法术,供君王采用。对于儒家,他是斥之为“蠹”——蛀虫的。韩非是一个聪明、深刻的人,对当时人情世故看得颇为透彻。他不相信人有美好感情,也不相信人可以经教育感化而为善,只相信赏罚分明,以利驱使人、以害禁制人。一部《韩非子》,构筑了一整套极端专制主义的、严厉控制人的方法和理论,读来令人不寒而栗。不过,对于研究政治学,这是一部极重要的书。
从文化思想来说,韩非鄙视一切属于艺术、美感范围的东西,是一个彻底的功利主义者。但他的文章很有特色。他懂得运用各种手段来阐述自己的思想。从逻辑的严密、论述的细致、条理的清晰来看,还要超过《荀子》;因为他喜欢把道理说得很透,一层一层地铺展,所以篇幅大多很长(如《五蠹》约有七千字);因为他的思想尖锐,又很自信,所以文风峻峭,锋利无比,语气坚决而专断。他还善于运用大量的譬喻和寓言故事来论证事理,增强了文章的生动性和说服力。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夫以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师长之智,三美加焉而终不动,其胫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易其行矣。故父母之爱,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严刑者,民固骄于爱听于威矣。故十仞之城,楼季弗能逾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主峭其法而严其刑也。(《五蠹》)
文章从常见的生活现象来推演重大的道理,可谓深刻明切。但取例极端也是一眼可知的。
楚人有鬻盾与矛者,誉之曰:“吾盾之坚,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难一》)
这就是常用成语“自相矛盾”的出处。原来用于攻击儒家同时赞颂尧的明察和舜的德化,指出二者不可能并存于一时,表现了韩非对于逻辑严密性的要求。其他如“守株待兔”、“郑人买履”、“滥竽充数”等,都是生动的寓言故事,至今仍被广泛引用。
《韩非子》标志着先秦理论文的进一步发展。其实,后世的理论文章,可以与之相比的也不多。
——以上采自章培恒、骆玉明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贴在此处,供有兴者参考。
|
|
|
回复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