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艺术笔记(二) |
二、艺术家的悖论
风舞落红 2003/5/1
1、 天书、鬼打墙
徐冰的http://red-petal.nease.net/image/artnotes/bigimage/xb-2.jpg" target="http://red-petal.nease.net/image/artnotes/bigimage/xb-2.jpg">《天书》(1988)和http://red-petal.nease.net/image/artnotes/bigimage/xb-3.jpg" target="http://red-petal.nease.net/image/artnotes/bigimage/xb-3.jpg">《鬼打墙》(1990)无疑应该算作中国现代艺术的两个重要事件,即使是十多年之后的我在参观广州现代艺术三年展时仍然可以得偿所见,由此可以窥见一斑。
徐冰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躲在房间里伪造汉字,最终形成了他著名的作品:《析世鉴——世纪末卷》。对于这一篇作品,尹有以下一段评论也许可供参考:
版画家徐冰的美术作品,铺天盖壁,源源而来。总题为《析世鉴——世纪末卷》,由版刻的方块“文字”组成。准确地说是由类似汉字又不是汉字、类似西夏文又绝非西夏文的无数个符号组成的一部庞杂恢宏的现代天书。你那顽固而又层出不穷的释读欲望遭到了硬性的阻截和无情的嘲戏;你那最终的失落感又无数次地从梦中走出,不断地把迟到的顿悟和苍白的困惑搅拌在一起,碰撞在一起。它总是让人升起对东方文化惯性的某种内心的警觉。它令人想象极不规则,四处爬行。那无法释读的荒诞的巨大组合,可以是经典、正史,可以是狂言呓语,可以是乾嘉学派小小瘦瘦的影子或寻根狂潮中的长吁短叹。一个人的困惑自有其因困惑而成活的幻想。但最重要的是在此你与幻象为敌——你不相信!你的实体在竖立着,并不因为精神上的东倒西歪而迷失了那种竖立感。但无法回避的异样展厅使你感到了毫无表情的版刻字符中的玄虚与嘲弄意味。难道这就是世纪末的真实感觉吗?!
不能释读的异样符号不断地重复、扩大,构成了一个困惑空间。你对释读习惯和释读意义的种种反思不都是产生在不能释读的审视中吗?优美利落的版刻技巧凝结在困惑空间中。而符号的汉字般的诱惑闪闪发光。释读的障碍百理不清、歧异丛生。或许这正史世纪末的某种感觉。“世纪末”让人无言以对。
如果说天书还能以它的民族性和现代性给所谓的文化人许多思考的话,“鬼打墙”绝对是冲击所有人艺术观的一件作品:1990年,徐冰在金山岭花了二十五天拓印了一段长城拓片。据说用掉了三百瓶墨汁、一千三百张高丽纸和书画纸,还有一群艺术家和雇佣的当地农民的幸苦劳动。一千多平方米的拓片全部用汽车运回。整个制作过程有着完全的资本主义式的“包装做法”,从计划、寻找赞助、制作制服、现场照相与录影、临时雇工、撰文发表等一贯作业,显露出当今资讯时代的精密效率精神(郭少宗,《“鬼打墙”作品“无意义”的质疑》,原载台湾《艺术贵族》1990年10月号)。
“鬼打墙”的视觉冲击力是惊人的。一段长城的各个立面平面展开图从天到地的倾泻下来,创意的大胆、时间的错位和它引起的有关艺术本质的思考无疑能够让人驻足停留。面对这样的作品,读者不得不去思考,这算不算艺术?即使有好的创意,是否仅仅只是复制一个历史存在的遗物就可以称之为艺术?
2、 无聊感和好的“度过”方式
徐冰拓印长城的动机,从《北京青年报》90年5月22日的文章《烽火台上徐冰谈艺》中,我们可以看出点端倪:
版画艺术是通过某种媒介的印痕而实现的。我感觉,世界上一切具有高地起伏的东西,都可以成为媒介,成为转印体。而把长城这样巨大的室外的东西挪到室内,在视觉上,心理上都给予人强迫感、令人震撼,这就是艺术的力量所在。
同时,我们希望这次创作具有行为性,是一个艺术活动,一个事件。有十几位朋友参与了这一活动,我们设计了专门的服装,并用录影、照片等记录过程,甚至把与之有关的一切痕迹,如票据、便条等都印成作品,与拓片一同展出……
实际上,艺术是么解决人类如何“度过”的问题之过程。我在寻找一种好的“度过”方式,最后又把它交给社会。我希望体会为一个没有意义的结果而付出巨大努力的过程,这本身就具有特殊的境界。
前面两段比较容易理解,既是对于版画艺术的研读和对于艺术行为的展示。但是他的第三段话,也就是“好的‘度过’方式”的说法,比较容易让人糊涂。尹吉男对此有一番解释:
1985年以后,我们对世界的感受发生了变化,纯情意识在下降,无聊感在上升。我们不相信任何超自然的力量,不相信无限,不相信梦想,这些原本是靠纯情力量带给人的一种幸福感。我们进入了一个理性的,同时又是琐碎的、冷漠的,同时又是焦灼的时代。许多严肃的现代哲学都不具有纯情意识,但都体现出对纯情意识下降的一种悲哀,这种感受在西方可能经过了几十年的渐变过程,而在中国本土则集中于很短的时间里。除了科学与无神论思想,其实在当代理性主义哲学家拆解纯情意识之前,尼采和弗洛伊德对之都进行过重大的拆解。当尼采说:“上帝死了!”它意味着西方人最先宣布具有崇高感的、超然的纯情意识开始化为乌有了。本来人的潜意识是极其神秘的,但弗洛伊德却把人类神秘的东西加以拆解,告诉你一切都是利比多和伊德在起作用。上帝死了以后,由什么来决定人呢?把你拆开了以后,明确的告诉你,就是这些东西,伊德和利比多来决定你。把人类仅有的那点儿纯情意识都给拆解了,把自我的那点儿情感堆积也给拆开了,现代的所有运动都不具有过去意义上的未来感,这是形成现代无聊感的根源之一。
我觉得应当把世纪末作为最悲壮的一幕来展开,作为沉痛的东西来展开;无聊感就是本世纪最沉痛的东西,只要你参与世界意识,你就会感受到这种东西。你以为是新的、最现代的,但实际上它是最无聊的;从情感上讲,越现代就是越无聊,彻底的现代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因为他是最无聊的。纯情表现的是一种常态、一种既定意识、一种传统性很强的东西,这种情感美妙地集中在古典艺术中。徐冰也曾说过:“我对现代的东西有兴趣,但当你在这些当今一流的现代艺术品面前时,感到的是低能、苍白和冷漠,远不象古典的东西那样感动你。这涉及到对古典与现代的认识问题,古典式的感动引起和调动你的情感。现代艺术只作为一种记录,它是人类思维阶段性进展的记录,它从根本上推进和拓展了人类的思维进程。”
有了无聊感,自然而然的就会想到如何去“度过”这种感觉,所以徐冰才会有“好的‘度过’方式”一说,所以尹吉男才会花诺大的篇幅来阐明这种无聊感。从刻印《天书》开始,徐冰开始尝试解决人类如何“度过”的问题。刻印过程一度使他减弱了“无聊感”,他自己“感到满足的是刻字的过程,在过程中我感到了封闭的魅力和自以为的崇高性”。为了摆脱无聊感而去寻找特殊的精神充实方式,对他来说,伪字的编造和刻制过程就变得极为重要了。同样,在拓印长城的工程面前,巨大的工作量和为之付出的艰辛,推论上也应该成为比最后得到的结果更加重要的过程。这大概是“度过”的一种方式吧?
3、 艺术家的悖论
徐冰制作《天书》的过程是他把艺术当作生活的重要过程,是他体会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这其中那个包含了企图追求崇高和永恒的认为目的,纯粹是与天书的伪造过程相联系的个人行为。这个过程一旦结束,意义就会分化。他说“作品交给社会如同把生灵赶入市场,它已经不属于作者自己了,它属于所有与它接触的人。它变得具体而又污浊,这使我想要离开它,再去僻静处找一个别的。”于是他开始拓墙。但是假如以“度过”为前提,同刻制天书一样,拓印长城也存在着过程与结果之间的矛盾冲突。
把艺术追求与人生追求搅和在一起可能是困扰所有艺术家或者艺术评论家的悖论,徐冰也好、尹吉男也好,都不例外。所以台湾的郭少宗才会在批评文章中指出徐冰应该“要么就是老实地拓墙作画不提过程,要么就是标榜过程中的无意义性而不留作品。”尹吉男也才会写道:“如果不去选择艺术结果,而只是去选择精神历程的持久性,这在实质上更具有艺术精神,尽管没有凝结成一个具体的艺术形式,但这种选择才具有真正的崇高和伟大。”所以尹以自己曾经写过的诗为证:
焦灼地等待
车的到来
把我拉到
更焦灼的站台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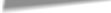 |
|
回帖 |
 |
|
| 回复人: |
黑鸦 |
Re:现代艺术笔记(二) |
回复时间: |
2003.05.10 12:59 |
|
想法多多,,,
不错不错,,,
现代这东西有太多多东西灌里面,,
不都开花,没花有过程,不接果,,什么东西都在异化着,,
|
|
|
| 回复人: |
wang131421 |
Re:现代艺术笔记(二) |
回复时间: |
2003.10.31 10:49 |
|
不错
|
|
|
回复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