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雾中偶得[转载] |
雾中偶得
老土
雾,漫天的大雾长久不散……这大概是几年来最大的雾了,尤其是在这个入冬之后的季节。
醒来,看窗外白白的有些亮度,便匆匆穿衣,走出户外,开始了自己的晨练。一走出楼道,就一下子走进了重重的大雾之中。明明是看到窗外一片白光的,怎么出来却是在雾里呢?略一寻思,我便明白了,这雾并不是很厚的,还不曾高过我居住的五楼。五楼之上是晴天,五楼以下便淹没在雾中了。在五楼居住,若有雾,便如在天上一般呢!我想。
但是,人是要在雾里行走的,比如我的晨练——每天十公里的慢跑。
雾大得要命。三步之外,便什么也看不见了。路灯依旧亮着,可是只能照在它身下的一点点地方。在这样的雾里行走,当要格外小心的。我还是在跑着,只是在慢慢地摸索着向前跑,紧贴着路边。身后时而会听到有人骑自行车的响动……
此时,大概正是许多学生上早间课的时候吧,他们使劲儿地按着自行车的铃铛,可是车速并不很慢。忽然有个孩子在前方摔倒了,并不厉害,我听见他哈哈地嘻笑着,扶起车子,骑走了。真是孩子!不知道深浅。摔了这一下,大概会骑得小心些了吧?
准时准点,在国道的那个路口,几位老年人出现了,远远地就听到了他说话的声音。每天都是如此,他们早早地起来,相约一起漫步。和他们每天都会相遇,可是我没想到这样的天,他们也会出来。走到近处时,我看到他们走得很慢,每人穿着厚厚的羽绒服。他们小心地向一边闪了闪,继续着他们小声的说话。老人,走过的路一定很多了,这样的一个雾天也许不算什么的。那么的一如既往,每天走着那段相约一起的路……
国道上仍有车辆驶过,开得很慢很慢。早早地就听见了车辆行驶的声音,可是直到近前了才看清是一辆大型集装箱货车,它所有的灯都开了,雾灯一闪一闪。重重的喘息,缓慢地爬着。它刚过去,后面又开过一辆,我这才知道那是一个车队。在这样的雾里开车,那是要有一定胆量的。
在路边停着一辆长途客车,所有的灯也全亮着,使劲地闪着,却显得那样的微弱。我想,这样的车,在这样的雾里,是一定要停下来的,无论你有多么紧急的事情要办,无论有多少人在远方的车站等着你,盼着你的归来。因为在它的里面,承载着许多的生命!
我继续向前慢跑着。在通向农村的小路上,又有一些人成群结队地在雾里骑着自行车。我知道,他们是进城的建筑民工。他们每天都是如此,从几十里地以外的农村,赶往城里,开始他们的工作。就为了那一天几元或者十几元的工钱,带着干粮和咸菜,不敢偷懒地干上十几个小时,在很晚了再返回农村的家里。而在这样的雾天,他们一定要起得更早才能正点赶到工地,晚上几分钟也许是一天的劳作都白干了呢!如此,我感到了生命的艰辛与不易,在他们外出劳作的背后,是一个个家庭。
在这样的雾里穿行的,大概还有着各种形形色色的人吧?人的一生,其实不就是在雾里行走吗?有谁知道自己的前方是一条怎样的路呢?在人们的眼前与心里总是充满着迷茫与困惑。
在不远处的路边,一个人在哈腰修理着自行车。自行车的后架上捆着一个大包。一问才知道,这位大伯是去赶往城里市场送蔬菜的,半路上自行车掉了链子。我忙上前帮他扶住车子。一会儿,车子修好了,他吃力地骑上,消失在雾里。没有一句谢谢,只是在他临上车时向我点了点头,嘴里嘀咕了一句:“这雾!”这雾是大,我没看清他的表情,他大概也没看清我吧?
雾,自然界中的一种自然现象。凡在这个世上活上些年头的人,一般是不会对雾感到陌生的。但人们是不愿在雾里行走的,因为它遮住了人们的视线。
返回的路上,有两个人骑着一自行车从我的身边经过,一男一女。“兄弟,青年路口还有多远?”男的问我。我凭着直觉说到:“往前约有一百米多吧!”他们虽是骑着车子,但并不比我快,几乎同行。不一会儿,我感觉走过了头,忙喊给他们:“不对,青年路口已经走过了,得往回走!”他们便慌忙下了车子折身向回走,并连声向我道谢。
在这样的雾里,走错路是丝毫也不会感到奇怪的。而且,在走错路的时候,往往是需要有人给指出来的。十四年前,我去青岛办事,也正是雾天,看不清路牌,对面过来一个人,我向前打听:“大哥,麻烦问一下,去信号山怎么走?”他用手指了指,说:“一直向前,再向左过三条街……”结果把我气得半死,他告诉我的正是相反的方向!至今也不明白,我对他已经很客气了,他为什么要骗我呢?他在欺骗中得到的是什么呢?
真正的雾并没有什么,倒是那些人为制造的“雾障”最害人了。也许我有些以偏盖全,但我确实是无法抹去那些最初的看法,对青岛人没有一点好感,持有某种不理解和偏见。
抬头向上望去,雾的薄处露出了半个淡淡的白月亮,可是瞬间便被又一层雾罩住了。想到还要和立勇一起去一百里外的张卫河畔登临舍利塔,脚下的步子加快了,不再去多想什么。
立勇在电话里说,你看这雾啊,不知何时能散了,怕是去不成了呢。我听了,就一再坚持自己的想法,雾总归是雾,怎么会散不去呢?已经定了的,还是不要改的好,那边的朋友在等着我们呢。他拗不过,就只好顺从了我,一起坐上了汽车。车外仍是大雾迷漫,车子行得很慢。只要能向前行进,就有到达的时候,我想。
大雾在接近中午的时候,才彻底散尽,一片明媚的阳光射进了车窗。一百多里的路程,整整走了四个小时,那里的朋友也等急了,直打电话。我就笑着解释说,人在雾里行,你能怪我们吗?
住了一宿,第二天一早,又是大雾。我们早早起身,去了临清市北郊的舍利塔。朋友说,若是晴天,在城里便可以望到高高的塔尖。走近舍利塔,我们便被它的雄伟与壮观折服了。舍利塔为明清万历年间一位和尚所建,历时九年,高九层。九,大概是取其最大的意思吧。我们打着手电,在塔里一层层地向上爬,心里说一定要上到最高层,去领略一下高处的风光。然而从塔顶层的小窗子向外望去,却是一片迷茫。朋友说,塔的不远处就是张卫河了,只可惜雾大,挡住了视野,晴天是很美丽的。
佛教中,讲究一个“禅”字,“禅”即是“悟”的意思。而此时的雾竟与这个“悟”字同音。看来这大雾是帮了我们的,是让我们在雾里去悟呢!当你用眼睛看不到的时候,也就只好用心灵去一点点地感悟了,感悟那就在不远处,却不能看到的风景。这并不是一件坏事,感悟的风景比真实的风景有时更具有魅力。感悟有时会出现与实际的误差,这也在情理之中。但各有个的美丽,我们无须抱怨这场大雾。
一个意外的收获,是遇到了来临清办事的老谭。他得知我们来了,便把随身带着的一本他最近刚刚出版的《读书的岐路》送给了我。老谭是个真正的读书之人,可是他为什么会走入“读书的岐路”呢?看着这样一个书名,让人如入雾中。读了他的文章之后方知,老谭实在是太过谦了,虽然谦虚是一种难得的品质。他说自己读书,有着很大的随意性,床头书案常常堆着书,高兴了就翻一下,如在乡野漫步,走到那里瞧一瞧,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又像饥饿的羊儿走进了春天的草地,毫不在意草的质量,这里一口,那里一口。缺少名家的指点,所以就慢慢地步入了读书的“岐路”了。
可是将这本书细细读了,你会明白,他并没有步入岐路。亏得老谭想出这样的一个书名,来迷惑读者!不过书读完了,便知自己是走进了一片雾中,又从雾中走出来,眼前霍然明朗。其实,我们读书和我们的生命一样,真的难免会走入岐路,步入了岔道。但那也是很难得的,有了那样一个不同寻常的经历。但是我们只要记住,迷途知返,才是最为重要的。
记起那天,雾已散尽,我们坐在返回的车里。老谭指了指车窗外那大片大片的树木说:“你们看,大雾给树们,不,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多么美的雾松啊!”举目望去,树们一片银装素裹!真是难得的一种好景致。雾曾让人迷茫,但它也给我们留下了美丽。老谭说,他回去一定要写写这美丽的雾松。美时刻存在着,关键是你能不能发现。
大雾散尽之后,雾松便成了雾的身影,留在了我们的记忆里……
故乡版权所有 Copyright 2002
粤ICP证030073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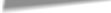 |
回复 |
 |
|
|
|

